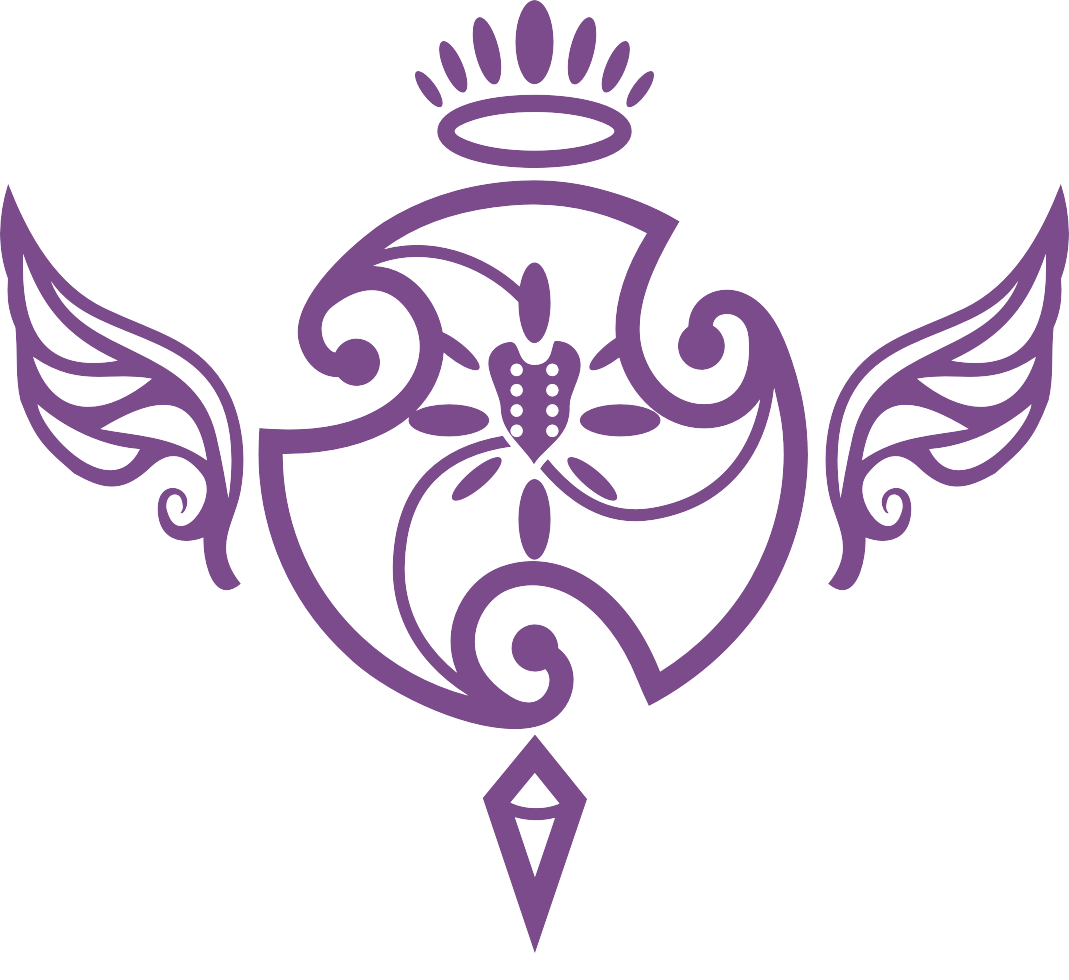道的傳遞 Transmission of Tao
原刊載於My Body Knows【幸福解壓】公眾號
看見我是誰
Radha老師的公開課終於做完了,我的內在多了一些放鬆,也讓我的覺知更加敏銳,我有更多空間來觀照這段時間以來我一直沒有好好去處理的一些情緒,都在這密集工作的幾周內被頻繁地觸發(Trigger),以至於我不得不去面對。
當時我跟平臺決定以隨喜公益的方式辦Radha老師價格不菲的公開課,因為這次傳遞TC能量的機會對我們來說是無價的(Priceless),我們相信會吸引那些對生命、對道、對靜心,甚至僅是對愛性有求知渴望的人們,我們想要打開那一扇窗,做那個橋樑,而我們也相信這樣的價值會在我們全然的投入與準備當中體現。
在招生與課程實際執行的過程當中,我們遇到許多非理想的情況,比如有學員一入群就打算白嫖,或者已經超過報名時間還一直發訊息試圖說服我為他們與其朋友們破例,彷佛我列出那些成年人該能看懂的規則只是我一廂情願地寫作,他們各自的個人需求應該淩駕一切。這讓我深刻感受到雙向聯結或一個信任的管道並沒有建立起來,因此,我不得不在最後一刻決定開課前才個別發會議連結給21號當天有足夠臨在(presence or availability)去接收資訊並回覆的人,至於那一天的生活或微信被其他事情佔據的人,也許是存在安排了更合適的管道供他們學習。
當然這樣的反市場操作引發了一點群憤,甚至有人不顧課已開始、我在為老師和大家翻譯,要不斷打電話到我已經開啟勿擾模式的手機直到它響起為止,跟地鐵上為了獲得母親注意而重複嚎啕大哭的孩子們如出一轍,雖然他們在外面都是擁有上百或上千跟隨者的「老師」,他們堅信在所有地方自己都該獲得特別的待遇。自然也有許多「療愈師」和「老師」們第一時間占了鎂光燈也沒有任何實質回饋。我分享這些不是要指責任何人的行為或無意識,而是這個過程讓我清楚看見自己對於任何非自律的發生有很大的不滿,甚至是憤怒。正因為我本身是個近乎無邊界式地為他人著想、極端獨立(或說孤立更貼切)且自律的強迫症患者,我樂意配合他人,對基層勞動人民特別溫柔(小夥伴常聽我接快遞員電話,都笑說小哥這會兒應該酥了),在治療師朋友之間更是有名的「付款積極份子」。我看見自己的小我不願意去理解、接受他人這些自動化索取且毫無付出意識的行為。
雖然我天天都靜心,我也能很快在意識上線後進入放鬆,但那頭腦的控制以及對於失控或失衡的批判依然活著,還是會時不時影響我,這些都跟我自身第二和第四脈輪的議題有關,關於認出需求、接受有需求、認同需求可以且可能被滿足,通過給予去分享、信任分享、輕鬆分享、有空間地分享、無條件地接收等。幾年前我和一名能量治療師在做遠距工作時,在肚臍中心遇到非常大的阻礙,大部分是胎兒時期母親的情緒毒素所致,當時對自己的靜心底子頗有自信的我,天真地說「不然我們先去存取心輪吧!」接著心輪的能量工作卻番出了更多不信任與空間被剝奪的嬰幼兒創傷,甚至還有受孕前的記憶。療程結束後治療師問我「心輪沒有想像那麼容易吧?」這讓我深刻意識到意識的工作是永無止盡的,任何自滿的感覺都是小我創造出來的幻象。Radha老師曾不只一次提醒我:Revati你對自己太嚴格了。我確實不需要如此嚴苛地看待自己或他人成長的過程,那會讓變形金剛般的頭腦更懂得如何巧妙地鑽縫隙,剝奪去享受放鬆與空的機會。
Radha老師的個案
我已經被問過好多次「Radha老師的個案是怎麼樣的?」
其實我給每個人的答案都不同,就像Radha老師開課前跟我說的,她不是一個「準備」來工作的人,她在「當下」工作。也就是說,無論是線下課程或者是線上講座,又或者是一對一的個案,每一個回應(response)都是當下那個片刻(in the moment)而非邏輯化、事先規劃的反應(reaction)。
在回答了十幾個人的同一個問題也生出十幾種說法後,我的大魔王頭腦也前驢技窮了。我想用一段Radha老師書裡的文字來傳遞個案可能的發生。
在講述帝洛巴系列時,當這些啟示闖入內在,我發現自己必須處理對於婚姻,相依偎以及安全感的想法了。
說明白點,我非常愛哥分達,想要擁有他的孩子。因為我每隔兩天就可以看到羅傑尼希,這似乎是另一個好理由,能坐在師父前面提問,並接受他個別的注意力。
「羅傑尼希,我跟哥分達很相愛,我真的想要一個他的孩子。」
他很嚴厲、很嚴肅的看著我。我想不管在那之前或以後,他不曾再那樣看過我。他說,『若妲,你自處的時候快樂嗎?』
那問題讓我意外,也把我推入心智上的空白裡。
我無法回答「是」,因為我之所以開始探索、追尋,就是因為我焦躁、不滿,而且通常都是痛苦的。我不真的快樂。但同時也很難說「不是」,因為我才剛說過跟哥分達很相愛,根據我看事情的方式,那應該會讓我快樂。所以我只能茫然的看著他,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如果你不快樂,那把一個孩子帶進這個世界有什麼意義?』羅傑尼希說那樣也只是將我的痛苦、我的恐懼往下傳給另一個人而已。首先,我應該先成為快樂的、滿足的,然後再去想孩子。『就現在而言,你先忘了吧。』
那像是個腦部手術,不痛但卻深入。
如同大多數義大利家庭的民情,我從自己還是個小孩時就開始照顧小孩。我有好幾個弟弟,另外還有表親生的侄女外甥們,一直都是我在照顧他們,當褓母、喂他們吃飯、帶他們散步,諸如此類的。很自然的,我也一直認為自己很有母性。
那是有生以來頭一次覺得,「我不需要做那些了」。有一種新的瞭解發生。在我、跟我一直攜帶的母性形象之間,已不再那麼相連。我可以把這二者完全分開來看。更讓我意外的是,母性的形象竟也是讓我無法成為自己的部分原因。
你一定有注意到,人們,特別是女人,不管在哪裡都被他們附近的每個小孩給牽動著。他們注意著小孩、抱他們、跟他們玩、逗他們笑等等。有些人也同樣這麼對狗、對貓或其他寵物。那並不表示他們對小孩還是動物有什麼由衷的連結;事實上,他們是想要跟某特定的存在以一種有意義的方式相關聯。
很多時候,那只是習慣:一個他們學到的角色,一種對不安全感的掩飾。那天傍晚,我看到甚至不是出於有意識的決定,我拾起這母性的形象好讓家人能接受我、覺得我有用。
從那一刻起,有好長一段時間,我甚至不想注意小孩,或把他們抱在懷裡。我想把空間留給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新領會。
不過情況在後來改變了。現在跟某些有個別連結的小寶寶,我發現把他們抱在懷裡是很美的感覺,但其他的我就不行了。不管是前述的哪個情況,重點是有意識的選擇,而非無意識的習慣。
那天晚上,所有關於我跟哥分達浪漫而理想的美夢被打破了。同時,帝洛巴的系列演講還繼續震攝著我。我幾乎可以想見自己就坐在這古老神秘家的面前,領受唯有在師父與門徒之間有著深度的親密與信任時,師父才會給門徒的饋贈。不管那奧秘的饋贈是什麼,我都覺得已經準備好要接受。
依附頭腦的人看不到超越頭腦的真理
在那兩個月之中,我覺得自己通過了許多測試,並相信我頭腦已經丟棄懷疑,到達了靜心般的澄澈。一點都不知道;就算在幾年後還是一樣,那習慣懷疑的頭腦會找到那麼多狡猾的方法來維護它自己。
不要對你的身體做什麼,只要放鬆;
緊閉嘴巴,保持寧靜;
放空你的頭腦而不用思考。
就像中空的竹子,讓你的身體輕鬆的休息。
這是帝洛巴用的一個靜心技巧:變成一根空心的竹子,空無的,放鬆的,接受的,不被活動佔據,也別無它求。
聽起來簡單。事實上,我也以為它簡單,但是它還是不容易,因為我們大部分人對空無都不能感到自在。這是竹子基本的品質:它是空心的,裡面空空的,我能看到它確實反映出人的狀態。
我們是皮膚、血肉、血液與骨頭,但是在我們存在最中心的地方,卻是空的。如果我們可以連結上這種空性,那裡就有可能變成充滿能量,無窮盡的能量以及未知的奧秘。那讓我想起,當初在我被要求傾瀉我的愛時,其中就有同樣的味道。用羅傑尼希的話來說,『空心的竹子變成了笛子,神性就開始吹奏它。』
就像嘗試其他很多方法一樣,我也實驗這空竹的技巧一陣子。但比起其他任何特別的方法或技巧,我更記得的是,那時包覆著我的,由帝洛巴大手印之歌在演講中與道場內衍生出的TC氣氛。
那時我有種感覺,「哇,就是這個!這真的是我的路。」
從那一刻起,不管羅傑尼希如何詮釋禪、蘇菲、道、瑜珈,或是其他任何靈性的道路,都無關緊要。我一直有種感覺,自己主要的道路就是TC之路。事實上,最廣意來說,TC可以延伸出來包含這所有其他的道路。
一個博學的印度朋友告訴我,TC (tantra) 這個詞來自梵文,那是印度最古老的語言;也是許多歐洲語系的源頭。
TC這個詞是複合字,譚 (tan),意思是「延展」,擴張或是變得透明,崔 (tra) 這個字尾則意指「一種辦法或是方法」。
因此「TC」這個複合字可解釋為擴張或是淨化的方法。換句話說,任何可以幫助個人經驗意識擴張的技巧都是TC法門。
這是非常廣泛的定義,我的猜想是,在印度早期的文化中,所有的靈修方法都被統稱為TC法門。舉個例子,儘管佛陀不屬於任何TC學派,也沒有公開教導人們關於蛻變性能量的靜心技巧,但佛陀在他的時代以「偉大的密宗修持者(TC行者,a great tantrika)」為人所知。一直等到有靈性教派開始劃分靈性與物質,將性與靜心分開來,提出獨身、克己與禁欲之後,TC才開始有了較狹隘的意思,意味著靈性上的「無二」途徑,即一切所有皆為神聖。
這樣說來,TC這個詞呈現出「法門」的意思─某種自我體悟的途徑,恰恰與瑜珈的道路相反,瑜珈是一種比較陽性的道路,要投注努力、掙扎、願力與戒律。TC被視為較女性與被動的途徑,主張感受力與接受性才是蛻變的鑰匙。
第三個意思,也是對我來說最有意義的,是「脈絡」,我想像的是將珍珠串成項鍊的那條看不見的線,因為TC最重要的是一種無形的傳承,像一條線,由師父傳遞給弟子,幾百年來一脈相承。如帝洛巴傳給了那洛巴,從那洛巴到瑪律巴,再從瑪律巴到密勒日巴,某些出自這脈絡的TC學派至今依然存在。
同樣的,從羅傑尼希對我、對其他人的傳遞中,我經驗到TC的鑰匙。當然,我知道羅傑尼希不只是狹義下的TC師父。他談過許多靈性道路,特別是禪,禪在他最後幾年公開演講中,變成主要的演說主題。
然而對我來說,羅傑尼希能涵蓋那麼多不同的蛻變方法,即是指出他是多麼偉大的密宗修持者(TC行者,tantrika)的象徵。
大家忘記了在西元十一世紀,生活在北印的帝洛巴,皈依的不只有傳統佛教,TC法門、哈達瑜珈還有其他眾多不同的技巧。他是個創新、不按牌理出牌的人,甚至後來還因為跟女人do i被逐出某個僧院。
如果帝洛巴可以被視為TC師父,我看不出將同樣的稱號延伸到羅傑尼稀有任何不妥,因為他們兩位都具備TC洞見的精髓:整體性,對生命的無二途徑,接受所有可用來擴展意識的方法,兼併神性與俗世,將性接引至超意識。
說了這麼多,有一點我得補充的是,當我來到羅傑尼希跟前,以及在我跟隨他的期間,我對研究TC歷史、學術與理智上的題材都沒興趣。我活在TC裡,呼吸著它。我從全身每一個毛孔中吸收它。從頭腦去瞭解TC只是我過程裡的一小部分。用帝洛巴的話來說:
凡依附頭腦的人,
看不到超越頭腦的真理。
也在同時間,我開始看見頭腦是怎麼對我玩把戲的,因為成為門徒的一個推論就是,開始為自己創造出一個形象,一個認真而專注的求道者。
我當然非常投入靜心,除了每天早上的動態靜心、每天傍晚另一個叫做亢達裡尼 (Kundalini) 的靜心技巧外,我還嘗試各種羅傑尼希在達顯和演講中提議的靜心技巧。
我沒打算要當門徒好幾年。事實上,我期望在幾星期或是幾個月內就悟道。因此在我裡面會有高度的緊張、嚴肅與期望也就不奇怪了,但那時我還沒有足夠的經驗來看到,這種態度本身對於處在「放鬆與自然」是多大的妨礙。
幸運的是,還好有羅傑尼希在那裡把我的雙腳穩在地面上。
記得有一次在帝洛巴大手印之歌的演講中,我有種完全消失的感覺,覺得好像已經離開了身體,處在身體之外了。身體完全靜止的坐在那邊─背部挺直,沒有一點動作與退縮─同時在裡面卻有某種東西從外看過來。很明顯,這是另一個可以讓我快點看到羅傑尼希的好理由,可讓我告訴他這個很棒的靈性經驗。
他看著我說,『不,不,不,那沒什麼。再等幾個月,在這裡待一陣子,我會教你真正的靈魂出體。你就會真的知道靈魂出體是什麼意思。』
我興奮了好幾個星期。遲早我會學到靈魂出體的。但那之後,隨著時間過去,我對這個密傳主題的興趣褪去了,我開始看到羅傑尼希在回應中有其不同的目的。很顯然的,他創造使我們頭腦上鉤的誘人情況,好讓我們待久一點,坐久一點,靜心久一點,以這樣的方式才能知道─或者起碼摸到邊─我們這趟印度朝聖之旅,只是為了來到內在的空性。
頭腦是不止息的產物,需要很多娛樂,所以有時候他會說些超自然的力量,或者神通 (siddhis) 來吸引住我們頭腦這部心智型的生物電腦。他並不支持大家學這類東西,但當真正的工作發生在另一個維度時,他淘氣的跟我們玩著,哄騙似的霸佔住我們的頭腦。
除了我提到想要小孩那次,羅傑尼希老是笑著我的問題。我說什麼都一樣,不管是很嚴肅的問題,還是半捏造的靈性經驗,他總是咯咯笑著,遊戲般的用笑容化解我的嚴肅。
慢慢的我瞭解到,在這條自己新發現的TC之路上最珍貴的鑰匙,是幽默,因為它能不斷的讓我如氣球般膨脹的「靈性自我」放氣。這意思不是說羅傑尼希貶低我投入靜心的誠意。相反的,他很鼓勵這一點。只是同時他要確定,我不會培養出讓自己僵硬且不自然的嚴肅靈性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