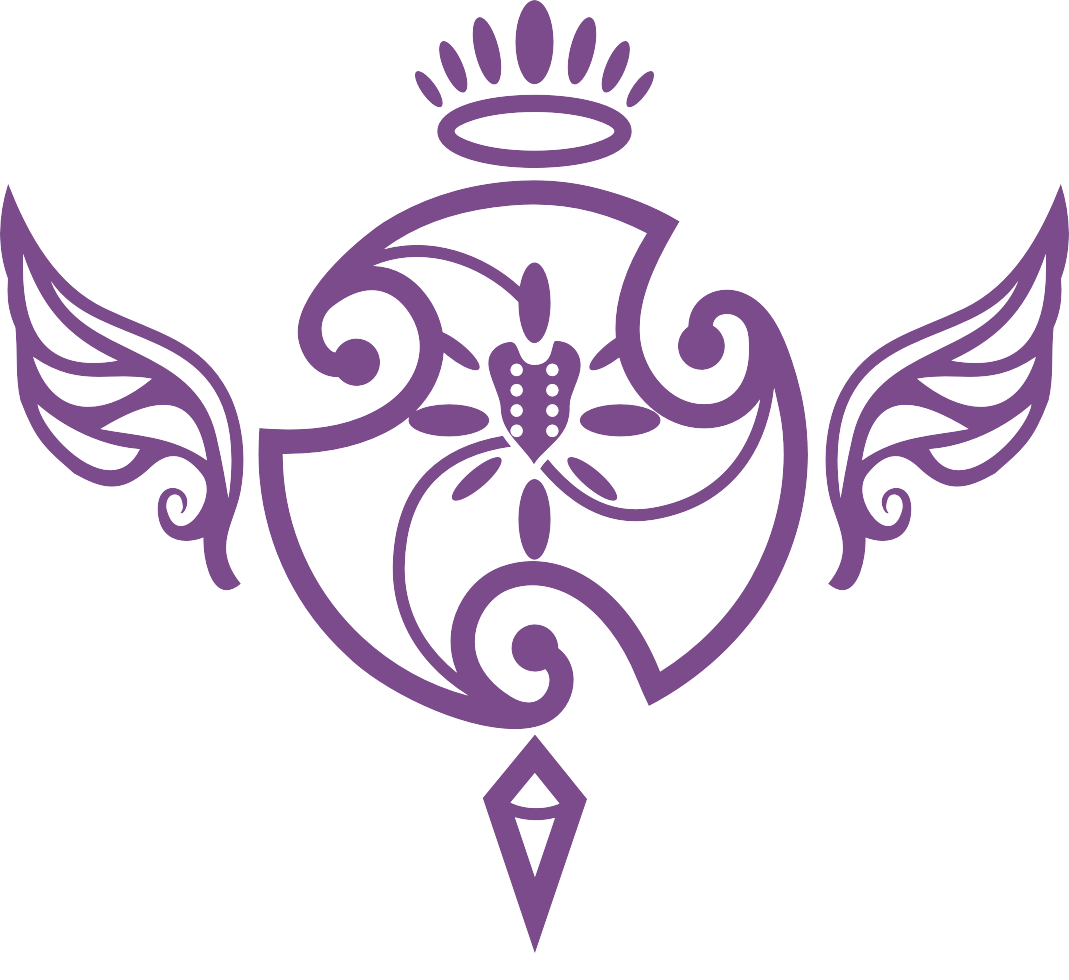觸摸是人類最早發展的溝通方式之一。自出生那一刻起,被擁抱、撫摸或安撫不僅帶來溫暖,更向我們的神經系統傳遞著關鍵信號,塑造著我們對安全感、聯結與信任的體驗。
然而對許多人而言,觸摸並非總是簡單尋常的體驗。無論是發展期創傷還是情境型創傷,都可能讓給予和接受觸摸的能力變得複雜甚至困難,並在身心留下持久的銘印。
理解觸摸創傷的科學原理及其背後的神經生物學機制,正是破解「人類聯結既令人渴望又令人恐懼」之謎的關鍵。
1 觸摸是生物本能需求
數十年的生物醫學已經研究證實,觸摸不是奢侈享受,而是生物本能的需求。缺乏養育性接觸的嬰兒:
- 會展現發育遲緩
- 認知障礙
- 情緒調節困難等症狀
這些科學發現顯示早期觸摸體驗是如何被編寫進人的神經回路:正面持續的觸摸能使神經系統培養出韌性,而忽視或侵入式觸摸則會讓身體持續處於防禦狀態。
曾經有一個女大學生參加我們的線下工作坊,想要學習親密接觸。因為長得很漂亮的她,不泛追求者,她也並不是那麼保守的人,卻總是在接近親密互動的最後一步,突然像著魔一樣,瘋狂肢體抵抗,嚇到伴侶也讓自己很苦惱。

她在課程裡,直接進入了醫療誘發因素的發燒,這就是她的身體對於親密接觸和打開身體感知的防衛反應。
斯蒂芬·波吉斯的多重迷走神經理論對此作出解釋:迷走神經調節著人體本能的安全感、社交參與度或人際互動裡的防禦狀態。
輕柔安全的觸摸會啟動副交感神經系統的「腹側迷走神經」分支,向身體傳遞環境安全的信號;反之,當觸摸缺失、不可預測或與傷害相關時,神經系統會默認進入戰鬥、逃跑或凍結的防禦狀態——這種生理銘印可能在創傷事件結束後持續存在於人的體內。
2 發展性創傷與觸摸回避的根源
對於經歷發展性創傷(忽視、照料情境不穩定或虐待)的人群,安全觸摸的缺失或扭曲會徹底改變身體處理關係信號的方式。
嬰兒大腦通過與照料者的共同調節來發展:通過懷抱、肌膚接觸和輕柔搖晃來建立信任與安全的神經回路。若缺乏這些體驗,身體可能發展出對觸摸的過度敏感或麻木回避反應。
我的課程和個案當中,比較常遇到這方面的情況來自於已婚已育女性,她們在經歷喂母乳的時候有很強烈的牴觸心理,甚至誘發更嚴重的產後抑鬱症。
她們說自己很愛孩子,但不知道為什麼身體就是不聽使喚,這也很大程度影響她們的乳汁分泌。
當然也有反向情況,原本對於肢體接觸不是很熱衷的女性,在懷孕生娃後激素變化、重新調和,反而在情欲和親密各方面都有了新的打開。這些過程若能有更專業的引導和軀體練習,都會有顯著的效果。
這不僅是「心理問題」。腦神經科學相關研究顯示,創傷會改變人掌控恐懼反應與社交參與的大腦區域(杏仁核、海馬體和前額葉皮層)的活動模式。
當事人可能頭腦認知上明白朋友的擁抱是安慰,但其神經系統卻將其解讀為威脅,從而引發焦慮或解離反應。這些具身化(embodied)反應會持續至成年期,影響人際關係、親密關係甚至醫療護理的進行。 這種身體本能的抵觸反應在公共場所的生理反應最為明顯。有些人不喜歡搭乘電梯,有些人很害怕地鐵擁擠,有些人則是身體嚴重解離到近乎體感喪失,總是會在人群裡東碰西撞,或者是踩到人,這種在動物界只有天災或被捕獵得逃亡時才會發生的行為,在現代人群裡卻經常出現。

3 現代社會的觸摸缺失
當代社會普遍存在的觸摸缺失加劇了這一問題。科技與機械產品在大眾消費領域的使用急速增加、城市生活的人際互動模式以及傳統文化中對身體接觸的禁忌,均導致研究學者所稱的「觸摸饑渴」。
即使沒有創傷史的人群,也會因缺乏身體聯結而感到孤獨、焦慮和抑鬱。對於有觸摸創傷的人而言,這種缺失更為強烈:渴望親密同時又恐懼親密。
疫情的經歷將這種矛盾凸顯到極致:不可避免的社交隔離剝奪了原本人類基礎的生理接觸,像是握手、擁抱、安慰性拍肩等可調節神經系統的日常觸摸。
許多科學研究發現此期間人們的壓力激素激增、睡眠障礙與心理困擾顯著增加——身體對觸摸的渴望不僅關乎情感,更植根于人類生存的神經生物學機制。
在後疫情時代最明顯的眼神接觸和生活互動變化就是很好的例子。在人臉辨識之前,人們去商店會跟收銀員眼神接觸甚至言語交流寒暄,現在同樣情境下人們傾向於回避眼神對視,甚至詢問快遞小哥或者是服務人員姓名「怎麼稱呼您?」,直接被拒絕的幾率要比過去高出許多,因為服務人員想要降低被投訴的幾率,他們將自己做為人當作是機器一般地提供功能性,自動省略了最基礎的人與人的聯結互動。
5 療愈之路:重建安全觸摸
腦神經科學的研究也帶來了希望。神經可塑性意味著觸摸創傷並非不可逆的終身判決。
安全漸進地重新引入觸摸的實踐能引導神經系統的重置。體現:
身心療法(somatics)
創傷認知瑜伽(trauma-informed yoga)
身體心理治療(body-based psychotherapy)
正是通過將觸摸與安全信號(平穩呼吸、平靜語調、眼神交流)緩慢結合,説明迷走神經從防禦模式轉向調節模式。
這樣的工作我們在關係諮詢裡大量的使用,特別是在伴侶因為親密生活不和諧而鬧彆扭的情況。
有部分的案主是因為小時候有被騷擾或侵犯的創傷經驗,導致他們的性需求會帶著一些控制甚至暴力傾向,即便女性也會。
而孩童時期缺乏母嬰互動的人,或者是被送離父母身邊寄養的人,則容易有性幻想症,並且對於手淫有很深的依賴,同時又帶著很深的罪惡感與羞恥感,導致建立真正健康的親密關係變得難上加難。這種情況我在未婚和已婚的男女身上都見過。
療愈的關鍵在於,在這個過程中必須尊重當事人的意願與節奏。
與嬰幼兒期不同,成年人有能力設定邊界、選擇情境並表達需求。
這種自主性正是療愈的核心,它能重建曾失去的主導權。即使非人際觸摸(重力毯、溫水浸泡或自我按壓)也能開始重建安全感。
重新思考人類聯結
大眾應認識到觸摸療法既強大又脆弱的本質:
它並非輕描淡寫可帶過的紙上談兵,更不是無章法就能執行的創傷救命丸——對有些人它能帶來治癒,對另一些人實施不當則可能造成傷害。
理解背後的神經生物學能培養一個人在關係裡跟社群的共情。
我們不應將觸摸回避視為冷漠,而應認識到這是身體的生存策略——神經系統在竭盡所能保護自己。
在工作場所、家庭和友誼中,培養尊重意願與敏感度的觸摸文化能減少誤解並增強聯結。
在醫療領域,承認患者具身化(embodied)的創傷歷史和知情的態度能使治療更有效更人性化。對個人而言,瞭解自身神經系統反應能開啟自我共情與漸進治癒之路。
6 結語:身體會銘記,也能重新學習
觸摸創傷不是抽象的心理問題,而是深刻的具身化(embodied)體驗。
它根植於人類發展的最初階段,經由神經系統回路經年累月的形塑,每一天都持續影響著每個人在生活中的人際互動、心理療愈與情感聯結的模式。
觸碰創傷的悖論在於:我們最需要的生理聯結,可能恰恰是我們最恐懼的。但借助科學洞察與共情實踐,我們終能解鎖這個悖論。身體會銘記,但也能重新學習——正是在這種重新學習中,觸摸有望不再是痛苦的觸發點,而成為通往安全感、親密與歸屬感的橋樑。